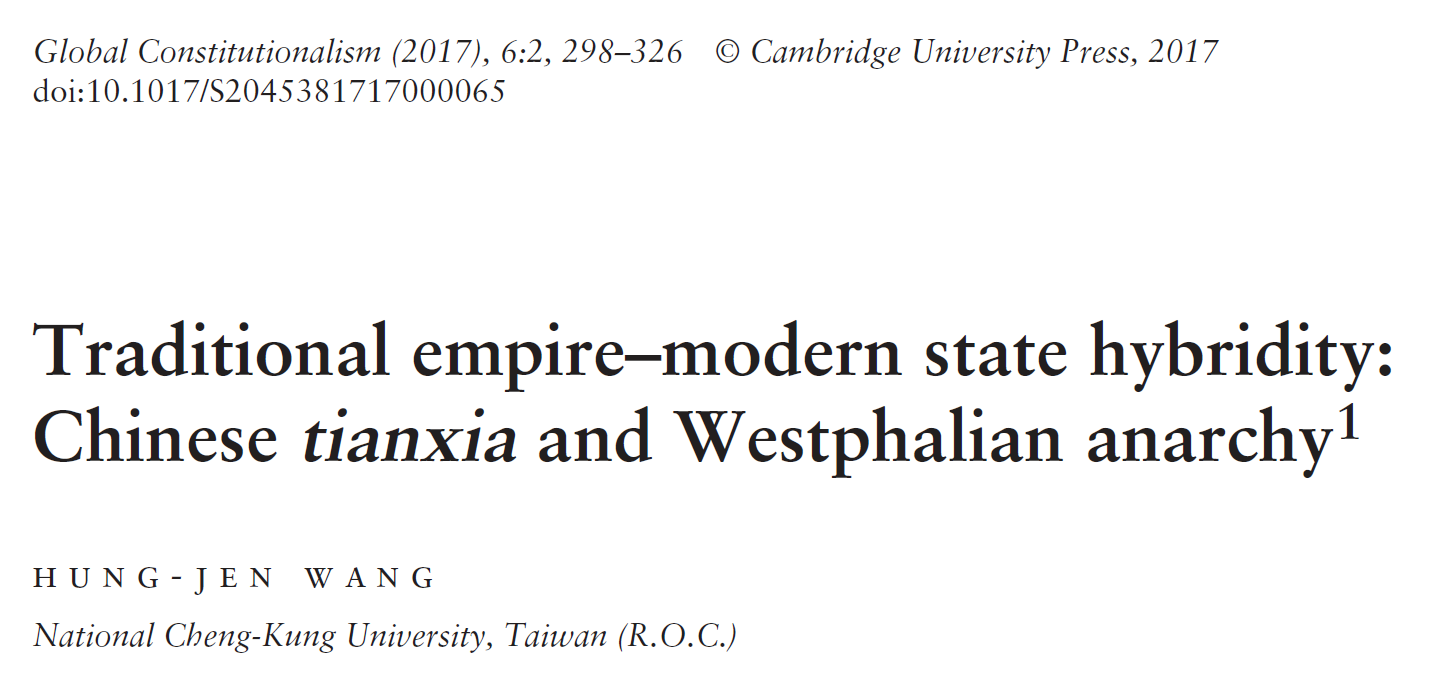共同體的未來 - 神話的力量和陷阱
在流散中,我們失去主場、語言與日常,但不代表我們失去解釋世界的能力。相反地,正因為我們離開了那個曾塑造我們的地方,我們更渴望建立一套新的理解、一套能讓我們在異地重新定位自我的敘事。也正因如此,我們極容易受到某些理論語言的吸引——特別是那些看似中立、理性、文化化的說法,卻實際上為壓迫提供了新的遮蔽方式。
一篇刊登於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的學術論文,由台灣學者王宏仁撰寫,試圖以一種「本體論混合」的方式,解釋中國對西藏、新疆、香港與台灣的治理。他主張,北京並非單一主權式的強制政體,而是一個融合了西方主權概念與中國「天下」傳統的治理模式。這種說法,聽來有文化深度,也富有理論吸引力——但對於我們這些來自壓迫經驗中的流散者而言,卻必須保持極高的警惕。
因為這正是一種神話建構的語言:它用理論包裝權力,把支配描繪成倫理,把抗爭描繪成誤會,最終讓強權得以進入我們的敘事空間,而不被辨認。
這篇論文說了什麼?
王宏仁主張,中國的統治邏輯並非單純的主權治理,而是一種「關係性秩序」的延續。他引用中國歷史上對邊疆地區的治理經驗,指出中國與西藏、新疆、內蒙古、台灣之間從來都不是以現代條約或契約形式建立主權關係,而是透過宗教冊封、政治認可、文化融合等方式,維繫一種長期的權力網絡:
西藏是「政教共治」的對象,清朝皇帝冊封達賴喇嘛,駐藏大臣是協調者。
新疆以部族協商與省制併存,象徵中央治理中的空間與彈性。
內蒙古延續盟旗制度,維持貴族自我治理與中央聯盟。
台灣是清代已納入的地區,戰後「收回」不過是歷史連結的恢復。
在這個架構中,中共不是破壞歷史,而是延續歷史;不是強制統治,而是文化性的治理延續。
他如何詮釋中共今日的治理?
王宏仁主張,中共並非斷裂性統治者,而是把這套「關係性治理」現代化。他指出:
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,是歷史秩序的制度化版本;
北京對台政策,是基於未竟的歷史關係,而非單方面統一意圖;
對於民族地區的語言、文化、制度設計,仍維持「差異性治理」。
他的論點是:我們不應該用西方的主權概念來衡量中國,而應從這種混合治理的本體論出發,看見其文化深度與治理複雜性。
這樣的說法,在許多對中國不那麼熟悉的國際讀者眼中,確實會產生某種說服力。
而這正是我們必須發出警告的原因。
問題出在哪裡?為何這種說法如此危險?
這篇文章的根本問題,在於它錯誤地處理了三件事:權力的位置、歷史的功能、以及語言的後果。
他把權力關係說成哲學差異
王宏仁將北京與四個地區的衝突說成是本體論的張力,是世界觀之間的碰撞。這種說法本身就抹平了最基本的現實:西藏、新疆、香港是被全面控制的地區,不是參與對話的對等主體。
它們沒有發言空間、沒有制度保障、沒有退出選項。這不是對等關係的衝突,而是單向壓制下的抵抗。
只有台灣具備一定的主體性,但即便如此,北京也從不承認。把這四個地方並列討論,是在製造對稱幻覺,把被壓迫的回應描繪成誤會,實際上消解了抗爭的正當性。
他把中國的話語操作當成治理原則
王宏仁說中國同時使用「主權話語」(對外)與「天下話語」(對內),是一種融合性的政治哲學。但事實上,這種話語操作根本沒有內在一致性。
北京在什麼情境下說什麼話,全看政治需要。 遇到外部批評,就講主權;遇到內部不滿,就講關係;必要時兩者並用。這不是文化融合,而是話語武器庫。不是治理模式,而是管控技術。
他把這種高度選擇性、策略性的語言操作,包裝成治理智慧,實際上是在幫統治權力建立話語遮蔽層。
他把壓迫與抗爭重新命名
對香港的處理最為明顯。他說香港人的不滿來自制度失靈、身份混淆、或對中央善意的誤解。他說「香港人只關心外交與國防,不理解什麼是主權」。這種說法完全忽略了 2019 年以降香港人的明確政治立場——我們反對的不是政策,是統治;我們拒絕的不是治理效能,是統治者本身。
他錯誤地把「不服從」描繪成「誤會」,把「拒絕主權」說成是「對自治細節的不滿」。這是再敘事(re-narration),是帝國語言最精緻的一種運作方式。
對流散者的警告
這樣的文章,會出現在國際學術平台上,被視為「文化視角」、「另類治理模型」,被引用、討論、甚至輸出。
而真正危險的是——它會被我們引用。
我們這些流散社群,也渴望敘事、渴望重新解釋我們的位置。在這個過程中,我們可能會不自覺地重複這種話語模式,把自己定位為「被誤解」、「等待再連結」、「尚未完成的關係主體」,而不是清楚地面對壓迫的本質與自我重構的責任。
我們當然可以談「未竟」、「倫理關係」、「記憶的連續性」,這些語言構成了我們新的敘事基礎。但前提是:我們知道自己正在建構神話,並對神話的力量保持警覺。不是讓它替我們抹去現實,而是讓我們有勇氣正視現實。
我們不能避免建構新的神話,但我們必須知道,神話一旦不自覺,就會變成另一種遮蔽。
最危險的神話,是我們自己講的
王宏仁這篇文章,不只是錯誤的分析,更是一種敘事形式的示範。
他讓我們看見,神話是如何在語言中重現,在學術中獲得通行證,在我們這些流散者的想像裡悄然生根。
如果我們不清楚界線,不保持警覺,下一個說出這種話的人,不會是王宏仁,而是我們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