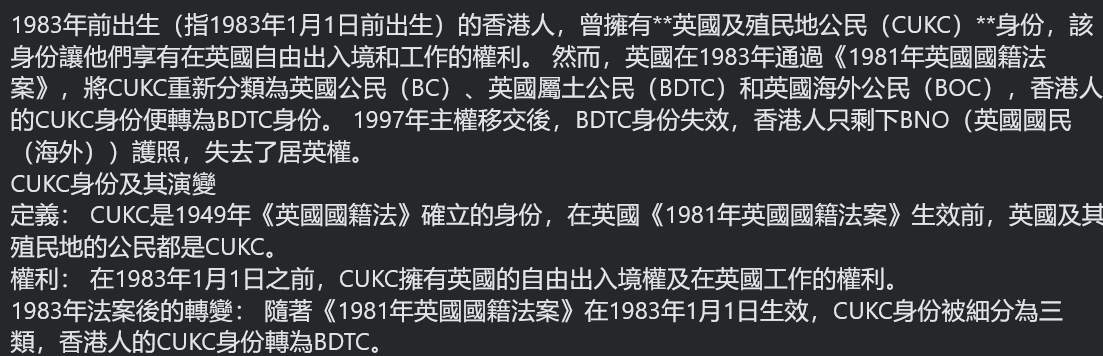不怕尷尬的平權
在公共討論中,任何人都可以主張政治立場——即使那是「天是黃色」的主張,政治容許幻想與情感。然而,一旦論述進入法律層面,語言的規則便完全不同。法律要求的是邏輯、定義與一致性。凡涉及法理推演,含糊與自相矛盾只會令主張者失去公信力。
近年圍繞「BNO 平權」與「CUKC 平權」的討論中,出現了大量歷史錯誤與法律謬誤。「國籍天生」與「CUKC 被細分為三類」等說法,是典型。
從專業角度看,這不只是錯,而是令人尷尬的錯。
「CUKC 被細分」:事實與法律的雙重誤讀
一種說法,指 1983 年《英國國籍法案》把「英國及殖民地公民」(CUKC)重新分類為三類:英國公民(BC)、英國屬土公民(BDTC)及英國海外公民(BOC),並稱香港人的 CUKC 自動轉為 BDTC。
這種說法在事實與法律層面皆錯。
首先,CUKC 並非「被細分」,而是被廢止。1981 年法案第 39(1) 條明確廢除 1948 年制度,自 1983 年 1 月 1 日起,CUKC 這一身分不再存在。其後設立的三種國籍,乃全新創設的身份分類,而非舊制度的延續或細分。
其次,並非所有香港 CUKC 均成為 BDTC。是否獲得 BDTC 取決於與某英屬領土的「連繫」(connection),並非自動轉換。更重要的是,自 1971 年《移民法》起,「英籍」已不再等於居英權。大多數香港 CUKC 在 1971 年後早已失去自由入境與工作的權利。
因此,所謂「1983 年被細分」與「失去原有居英權」的敘述,實屬虛構。事實上,那些權利早於 1971 年已不存在。
「國籍天生」:誘人修辭,荒謬法理
「國籍係天生的權利」這句話,表面上像是對殖民歷史不公的抗議,聽來理直氣壯。但從邏輯上推敲,它自相矛盾。
若「國籍天生」是法律事實,那就表示國籍不需立法確認。然而現實上,無論是 CUKC、BDTC 還是 BNO,皆源自英國國會立法而存在。若國籍真是「天生」,便不可能由議會創設。
若「國籍天生」是道德主張,即認為「國籍應當自出生享有、不可更改」,那麼任何要求英國以新立法「恢復」或「平權」的訴求,也同樣陷入邏輯困境——既然天生,就不應須法律改動來「修正」。
換言之,「國籍天生」在法律層面既不成立,在邏輯層面亦不能自圓其說。把這種修辭用作法理基礎,暴露論者對基本法律結構的誤解。
錯得令人尷尬:當倡議失去專業紀律
從專業角度觀之,這類謬誤之所以令人尷尬,原因有三。
其一,暴露對法理的無知。
法律是一種語言,講求準確與一致。當有人把「國籍天生」這種修辭語當成法律命題,或把「CUKC 被細分」誤說成法律事實,任何具法律訓練的人都能一眼識破。這種錯誤不是「意見不同」,而是對制度結構的基本無知。
其二,是誤導公眾。
錯誤的法律敘事會製造虛假期望。當公眾被誤導相信「1983 年前人人有居英權」、「2002 年升級應包括香港」之類的說法,最終發現皆屬誤導時,信任與公信力便一併崩潰。
其三,是對專業社群的損害。
對法律界而言,看到這些不符事實的論述,無異於看到一場自我羞辱。任何真正熟悉英國國籍法的人,都明白 CUKC 的廢止、1971 年的轉折及 1981 年的重構。當倡議者在未理解法理基礎的情況下,引用《國籍法》條文或國際公約,只會令人懷疑其專業誠信。
《R (APD) v SSHD [2025]》
2025 年的高等法院判決 R (APD) v SSHD [2025] EWHC 246 (Admin) 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界線。法院明確指出,《1981 年國籍法》第 4L 條屬個案性、反事實推斷的補救機制,並非恢復舊有國籍的渠道。
第 4L 條只適用於個別情況下,因歷史歧視或行政錯誤而「本應」取得國籍的申請人。它不是為整個群體「平反」的工具,更不可能用以重建早已廢止的 CUKC 身份。
換言之,若把第 4L 條當作「平權法寶」或「恢復英籍捷徑」,不僅法理錯誤,亦違背判例精神。如此誤用,只會進一步削弱運動的可信性。
法律語言失守
一旦錯誤與矛盾成為運動的語言,運動便失去嚴肅性。當倡議者聲稱「要以法律途徑爭取平權」,卻連基本法律概念都搞錯,整個運動便變成表演而非論證。
真正的尷尬不在於主張被否定,而在於論證失格。
在法律世界裡,精確與一致是最低標準;錯誤的語言、錯配的概念、混亂的邏輯,只會令整個倡議變成笑話。
政治可以容納情緒與口號,但法律不能。在英國國籍法的語境下,「CUKC 被細分」與「國籍天生」這類說法,不僅違反事實,更違反邏輯。
一場本可建立於理據與證據之上的討論,被這類錯誤佔據,結果是言者厚顏,聽者尷尬。